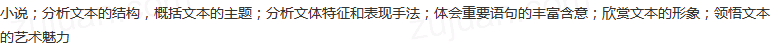复活(节选)
列夫·托尔斯泰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想着心事。
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要么嫁个长官,或者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
她想到许许多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地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未来的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名字)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作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卡秋莎虽然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卡秋莎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打牌。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着椅背,不知在笑什么。卡秋莎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火车缓缓开动了,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粗暴地把窗子放下。
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地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中,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玛丝洛娃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玛莎害怕了,搂住她湿淋淋的衣服,“阿姨,我们回家去。”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卡秋莎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她打定主意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中,匆匆走回家去。
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她不再相信善了。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