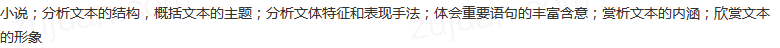文本一:
人世间(节选)
梁晓声
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挂在墙上。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常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稀里哗啦踏烂了。”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么泥泞不堪了。”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的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不论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街坊家临街墙面的义务抹平,他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抹墙需几道工序,先得备下黄泥,还得有足够的麦秸或谷秸往泥里掺。和好一堆抹墙的泥很需要力气,他和不动了。黄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黄泥的地方越来越少,那种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现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干砸垒的黄泥小屋。当那些小屋住进了人家,如果谁还去周边挖取黄泥,常常引发严重冲突。那些人家会形成一种占山为王的领地意识,攻守同盟,态度凶悍,让企图分享公共资源者望黄泥而却步。
周志刚是洁身自爱的人,当然避免自取其辱。缺少了黄泥,不论他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他们那条脏街所进行的面子工程,都只好停顿下来。毕竟他只是一个老迈的改良者,也只有点儿人生余力做改良者。倘要彻底改造自己家及那条脏街的面貌,需动用推土机和铲车,需有充足的建材,还需有一支建筑队——而单枪匹马的他只有一把抹板,街坊们心劲儿又不齐。对他们而言,维修自家房屋是分内之事,至于那条脏街已经那样了,可以怎样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虑范围。他们认为那纯属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觉得有失面子,他们则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么脏乱差的地方的人家还有面子值得在乎吗?还讲得起面子吗?讲面子起码也得有黄泥呀,连黄泥都稀缺了,就只得让面子见鬼去了。墙皮掉得太不成样子了,才趁夜到这里那里去偷黄泥。倘谁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后挑着水桶走往与水站相反的方向,那么准是到什么地方偷黄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坊们对此心照不宣。偷黄泥往往引发人身伤害事件,但由于是刚性需求,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周志刚断不会做那种勾当。他连自家墙上掉下的墙皮也宝贵地留存起来,积少成多,以备用时。他不敢放在门外,怕被偷,专门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节假日,儿女们回来看望他和老伴时,他嘴里常常会忽然蹦出一句话:“你们谁知道哪儿有黄泥吗?”
儿女们便都装聋作哑。
他是在儿女面前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不会问第二次的,总用自言自语缓解自己的担忧:“这个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个家了。”
(有删改)
文本二:
在社会和时代面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它从价值取向上,彰显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做一个好人,是对人性、人心的内在要求。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人世间》里无时无处不在体现这种思想的光辉。
我们从《人世间》中不难看到,当生活中的矛盾处在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与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以周志刚为例,在没有见到女儿周蓉之前,他对女儿不管不顾跑到贵州山区投奔“右派”诗人一事,怒不可遏。等到他见到了这位诗人,看到了女儿的生活现状,他原谅了女儿,理解了女儿,一场潜在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同样,当他得知自己的小儿子与怀着他人骨肉的郑娟相爱时,周志刚也是愤怒至极。他了解到郑娟的付出之后,他帮小儿子整理行李和洗漱用品,把他送往郑娟家里。他对周秉昆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恩不报,那是不义。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而且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而周秉昆原以为是父亲要赶他出门。这个时候的他,泪如泉涌。
一位深明大义的父亲,看重的是在困难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助和相互守望,更有应该尽到的为人的责任和担当。
正是这样,梁晓声把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让人物立起来说话。呈现现实,同时从理想向度上引导现实,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梁晓声说过的四句话,被广为流传:“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一些人以为这是他对文明、文化的定义,其实这是他从文明、文化的角度,为“好人”定下的标准。从这样的好人标准出发,希望人性向上、向善,社会向美、向好,这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深厚内涵,同时也是《人世间》的深刻魅力。
(摘自李师东《梁晓声〈人世间〉:现实主义的新高度》)